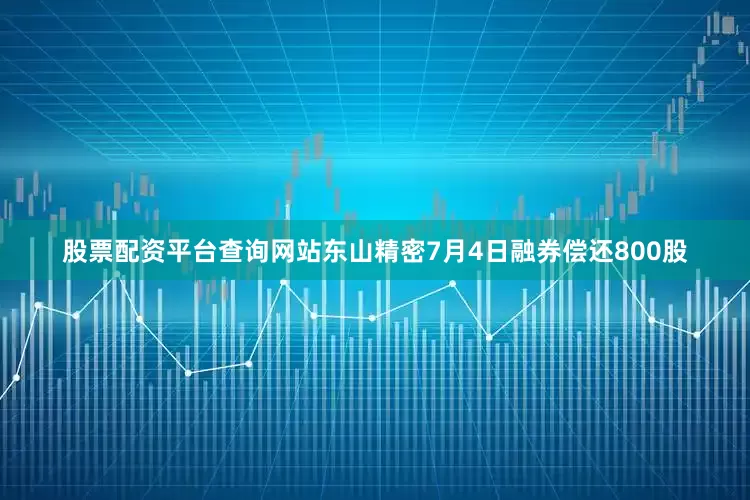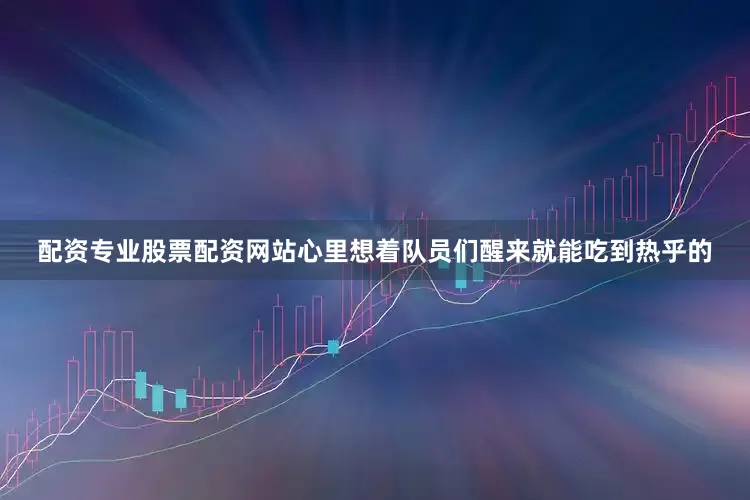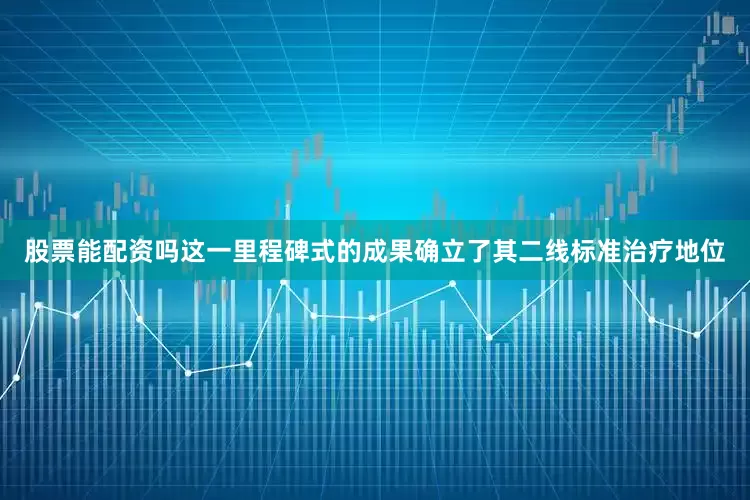卢俊义、栾廷玉、史文恭等八大势力头号名将的命运浮沉
说起《水浒传》里那些刀光剑影,小时候我在外婆家看过老版电视剧,印象最深不是宋江,而是那一帮各自为王的“地头蛇”——梁山好汉固然威风,但每个势力都有自己的压箱底人物。要论谁才是真正的“一把手”,还真得细抠细节。有一年春节回乡下,村里老人还跟我念叨过:别只记着林冲、鲁智深,其实卢俊义才是梁山武艺最顶尖的。后来查了点旧书野史,还真有不少冷门讲法。

先说梁山这摊子事儿。晁盖死后,那会儿宋江想找人替他报仇,看来看去都觉得林冲关胜不够硬气,于是就盯上了大名府那个生意做得飞起的大户——卢俊义。据说当年京东一带还有顺口溜:“棍棒无双数二郎,大名富商镇北方。”就是指他。这人武功高到什么程度?连秦明这种猛将,在曾头市碰见史文恭都被打得没脾气,可卢俊义却能和史文恭拼个旗鼓相当。
不过,说来也怪,宋江为了拉拢卢俊义进伙,还搞了一出反诗陷害,把人逼上绝路。我爷爷以前翻烂的一本《水浒全传》旁批写着:“世道险恶,人心难测。”倒也应景。最后还是靠吴用和李逵下套,把这位二郎请到了梁山。而且,据乾隆年间刻本记载,当时宋江放走了管家李固,就是故意让官府捉拿卢俊义,这段很多评书先生爱加油添醋,说“兄弟情薄如纸”。至于后来活捉史文恭,为晁盖报仇雪恨,这事成了他立身之本。

招安以后,本以为可以熬出头,不料庙堂之高远比绿林险恶,高俅杨戬这些权臣暗中使坏,用毒酒送走了这个曾经的大英雄。我妈年轻时听老邻居讲过,“英雄落幕多半不是死在战场,而是杯中物”,想来确实如此。
再往南一点,就是祝家庄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的恩怨。在我们县城周边,还有座小村叫祝家楼,据说原型就来自这里。当初祝家庄三兄弟横行一方,但真正能打的是教师栾廷玉,他师承少林外门拳法,有种传闻说栾氏祖籍河北清河,一支流入山东沂蒙山区,因此当地还有些“栾拳”的套路流传下来。不过再厉害也扛不住群狼围攻,被乱军砍死的时候,有个逃出来的小厮后来给后人留下一句话:“教头虽勇,无奈众寡悬殊。”

至于李应和扈三娘,他们其实早就对祝彪不满,一个被打伤,一个投降未果,都成了局外人。有意思的是,我小时候听戏班老师傅唱《扈三娘大战孙二娘》,里面还夹杂一句,“女中豪杰难敌天命”,颇有几分宿命味道。
曾头市则更像是一座黑色幽默剧场。主角当然非史文恭莫属,此人在地方志上偶尔还能找到点蛛丝马迹,比如《东平州志》提到“昔有善射者,姓石名某,以箭术闻于时”。有人考证可能就是他的历史原型。他杀晁盖那一箭据说明朝末年的民谣里都还有残句:“黑夜藏弓影,一矢断英魂。”可惜终究没躲过去,被活捉剖腹祭奠晁盖,也算因果循环吧。

轮到朝廷阵营,要挑第一高手,多数旧小说评点都推崇周昂。这位禁军副教头,其实身份很微妙。他既是体制内顶级武夫,又始终游离在政治漩涡之外。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甚至提及,当年汴京城北校场常见周昂演练枪棒,引得百姓围观啧啧称奇。“兵器声响处,人马如云集”——画面感十足。他与卢俊义斗个平手,也是彼此惺惺相惜,只不过世事无常,他最终选择急退保全性命,没有留下太多传奇故事流传下来。
辽国方面,那兀颜光可是铁骑中的狠角色。一些辽金边境地区,如今仍流行关于兀颜家的民间故事,说他们祖上擅长马上枪法、阵前破敌。在正统版本里,他摆出的太乙混天象阵,让不少读书人联想到诸葛亮借东风,不过最后还是被关胜斩于马下。有趣的是,《契丹古志》隐约提及一个叫乌延广的人物,与兀颜光名字音近,不知是否同源异脉,总归都是草原上的悍将形象深入民心罢了。

田虎麾下那个孙安,是属于典型“大器晚成”类型。据坊间野谈,有一次孙安与秦明激战五六十回合,两败俱伤,却结下私交;等遇到更强的对手,如卢俊义,每次都是僵持几十回合收场。有专家考证认为,这类描写其实折射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之间尚武精神遗存,因为田虎造反地盘就在今天晋冀交界处。不巧的是,好汉们征讨王庆前夕,孙安突然病亡,没有机会善终。当地主持丧礼的人还特意烧了一把断柄钢刀作陪葬品,以示其生前未尽全力之憾(据康熙年间地方笔记)。
王庆集团里的李助,自号金剑先生,是唯一一个靠速度吃饭的大侠。《剑谱拾遗》中甚至附带描述其用剑快如闪电,只可惜遇到了公孙胜施展妖法,一招失手丢掉性命。同伙杜壆也是硬茬子,与鲁智深齐名,可惜架不住双拳难敌四手,被联合绞杀而亡。这类人物往往没有多少后代资料留下,只在一些偏僻祠堂壁画或乡野轶事中偶尔现身,比如苏皖交界某村墙壁残存墨迹,就画着一个腰佩长剑、自负潇洒的人物像,上题“小金”。

最后该聊聊方腊那拨八大高手,其中石宝堪称压轴王牌。据浙江建德县老人口述,相邻几个小镇每逢农历五月都会舞龙灯纪念石宝,说他虽为逆贼,却忠肝烈胆,对抗官兵从未退缩一步。《临安县志》卷七记录:乌龙岭自古易守难攻,“昔有南离将军,自刎其颈,不辱降贼”。索超邓飞等好汉皆折损其手,可谓凶神恶煞般存在。但结局依然悲壮,到底逃不过孤立无援、自裁谢幕这一遭。从此之后,当地茶馆闲话便添上一句俗语:“宁做石宝守岭鬼,不做庙堂笑面佛。”

多年以后,我偶尔路过建德,在一家米粉店喝汤聊天,还碰见老人摇着蒲扇唏嘘感慨:英雄末路,各归尘土罢。“你看现在谁还信这些?但咱们这代人的童年,全系在这些故事里啦!”窗外阳光照进来,也照亮桌上一碗已经凉透的小米粥,就像那些逐渐消散在人海里的名字一样,再无人问津,却又总有人偷偷怀念。

内容来自公开资料与个人见解,仅供学习交流,不构成定论或权威史实参考。
在线开户股票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可靠股票配资 李彦的履历颇具看点
- 下一篇:没有了